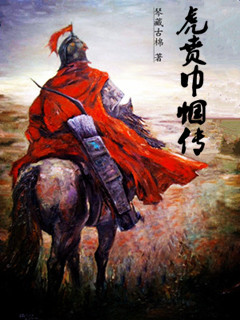五月的终南山,千峰碧屏,云缭翠障,烟霞绮丽,飞瀑跃虹。
山中腹地南梦溪,藤萝茂竹,隐天蔽日,山风过境,林涛阵阵,溪水石潭,静影如壁。
李家庄园便坐落在这南梦溪的青山绿水之间。
辰初时分,霞光如练,李三娘执绺向前,引着李家车队穿梭在密林之中,只见她身着紧袖短紫衫,头戴皂罗折上巾,腰挂棠溪佩剑,肩背白桦角弓,男仆婢女们紧随其后,护着车队向庄园缓缓行进。
李三娘满脸肃然,不时回望车队,千分牵挂,万分纠结,如密匝匝的针线,深深地刺在她的心头---五弟李智云生死如何?夫君柴绍现今可好?大哥四弟是否平安……
然而,眼前一家老小数十口人,却由不得她半点分心,纵然戎装加身,刀剑在鞍,依然双眼警惕,没有丝毫松懈。
正在行进时,前面突然传来“笃笃笃”的马蹄声,数骑迎面驰来,李三娘眉头一皱,勒马立定,举起右手,警示众人,婢女们立即张弓搭箭,钱大柱则率领男仆们拔刀相向。
“主子---小奴来接应你们了!”原来是马三宝和几个随从赶到了。
来到跟前,马三宝翻身下马,跪拜问安。
“三宝,你们辛苦,从蒲津渡过来,一路可好?”李三娘问道。
“好哇,在蒲津渡的船上,远远看到阴世师的追兵上了钩,我们几个高兴得跳了起来,都说主子们的谋划好,都盼着您和家人们早点过河哩!”马三宝自顾高兴,没有注意到李三娘忧心忡忡的模样。
“你们几时到的?回庄里去看看没有?”
“我们几个轻车快马,昨日就到了,庄里……”马三宝抬起头来,脸上愁云密布,顿了顿,“庄里和前些年不大一样了。”
“怎么不一样了?”
“哎,主子,一言难尽啊,您回去看看就知道……”
一路上,李三娘沉默不语,只是赶路。
马三宝跟在后面,和钱大柱聊着路上发生的事儿,当他得知李智云在风陵渡口被擒时,惊讶得张大了嘴,半晌儿说不出话来,望着李三娘的背影,难过地垂下了头……
峰回路转,绿树成荫,半个时辰后,一处松木门头已映入眼帘,上面挂着“李家庄园”的黑底镶金牌匾,字体矍铄,漆底斑驳。
松木门头上架着褪淡的朱色梁枋,梁枋拱挑屋檐,屋檐下雕花垂柱上刻着几只锦鸡,栩栩如生。
李三娘驻马凝视,百感交集,这牌匾,这梁枋,这雕花,出阁前的记忆顿时涌上心头,和女伴们浣纱濯足,斗花斗草,投壶雅歌,嬉笑藏钩……
“三娘,我的好妮子啊,你们可回来了,唔……唔……”正回忆时,耳边传来一个老妪的哭声。
李三娘抬头一看,原来是自己的乳母赵嬷嬷,正擦着眼泪朝自己走来,她的身后跟着百十来个妇孺老叟,拄着拐仗,抱着孩子,面黄肌瘦,颤颤巍巍地跟着走过来。
李三娘立即翻身下马,快步上前,搀着赵嬷嬷嘘寒问暖,数年未见,一朝相遇,彼此都是泪眼朦胧。
“嬷嬷,您老今年五十有六了吧?身体看起来不怎么好啊?庄子里怎么就剩下老弱妇孺了,其他人到哪里去了?”李三娘挽着赵嬷嬷,边走边问。
“妮啊,你们走时,庄里是人丁兴旺哩!打皇帝征伐辽东以来,官家年年来抓丁派赋,前番去的二三十个后生,一个也没回来,听说……听说都殁在鸭绿江里了,可怜我家四郎,才十六啊……” 赵嬷嬷老泪纵横,哽咽不已。
“嬷嬷,你们如此艰难,怎么不派人到河东来找我们呢?”
“找过的,先前老太爷给咱们接济了些粮食,后来,仗打得远了,联络不上了;河东的大爷也曾派人送回些银两,但年前官家把黄河封锁得紧,便断了消息。”
“嬷嬷,我们回来带了些细软,可以顶一些时日的!您老别难过,大家在一起,众人拾柴火焰高,我们从长计议,好吧?”
“嗯,你们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啊,咱有靠了。”
娘俩儿相携相倚,边走边说,引着车队朝庄子里走去。
路边,野草没膝,茅舍零落,墙垣塌陷,庄稼地里一片荒芜,车马走过时,惊起林中一群白脸山雀“噗噗”地冲上天去。
……
时间飞快,一晃便过去了五、六天。
这几日,李三娘带着家人修葺屋舍,打扫祠堂,访贫问疾,施粥舍食,抢着时令在地里撒些瓜菜种子,忙得两头摸黑,双脚踮地,连日下来腰酸背痛。
“凤鸢,你去把晾好的衣物收进来;巧珠,来给我揉揉臂膀吧,”李三娘正在吩咐两个贴身侍女时,只听到屋外传来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。
“谁呀?”
“请问柴夫人在吗?老翁有事相告。”
开门看时,一个年过七旬的老者倚仗而立,脸颊瘦削,须发皆白,目光炯炯。
李三娘认得,这是庄子私塾里的向先生,连忙请进屋里,看坐上茶。
向老翁凭几坐定,笑道:“柴夫人,此番回庄里,未见大爷和柴官人,我老者昏聩,冒昧相问,几位爷儿安好?怎未一同回来?”
李三娘稍理云髻,微微一笑,答道:“向先生,皇帝诏告天下,发兵救援东都,大哥他们都应诏奔东都去了。”
“哎,东都可救与否,老天才知晓啊!”
“向先生,此话怎讲?”
向老翁拄着拐仗,站了起来,缓缓说道:“‘皇天无亲,唯德是辅’,自大业以来,您看天下都给折腾成什么样子了!可怜庄里的那几十个后生,此去辽东必无生还之理,留下些孤儿寡母艰难度日,”向老翁顿了顿,目光一斜,瞅了瞅屋里的凤鸢和巧珠。
“不打紧的,向先生,她们自小便跟着我,都是贴心的人儿,您老有话,不妨直说。”
“好,柴夫人,恕老夫斗胆直言----大爷他们此行不应向东,而应向北,到晋阳去,同老太爷和二爷会合!”
“向先生,他们不去东都而到晋阳?”
“正是如此!敢问柴夫人,东都因何被围?民不聊生,百姓揭竿而起呀!前有楚国公杨玄感起事,现在又是瓦岗寨李密得势,在老夫看来,天下纷乱如此,恐将不再姓杨了,而老太爷手握重兵,驻守一方,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啊!大爷他们不向北去而往东行,实在……实在不明智哩!”
李三娘听闻,满眼欣喜,站起身来,说道:“先生睿智!实不相瞒,大哥他们的确是奔晋阳去了。”
“好哇,好哇,只是……”向老翁捋捋白须,看着李三娘问道:“您可曾想过,晋阳若行大事,这南梦溪的李家庄园便成是非之地了,如何自保呢?”
李三娘捧起茶碗,端到向老翁面前,说道:“先生,这也是忙碌之余,这几日我正在思索的事儿呀,只是尚未想透彻,还望先生赐教!”
“柴夫人,这终南山纵横数百里,自古便是藏龙卧虎之地!大业以来,赋重役苦,征伐不断,男儿们不是战死沙场便是逃役山间,就咱南梦溪这百十里内,便有数支绿林队伍出没其中,实话相告吧,我侄儿向善志便在其中,已有数百人马了!”
李三娘眨眨双眼,全神贯注,侧耳倾听。
向老翁见状,点点头,继续说道:“李老太爷当年为官陇岐,善抚百姓,甚得众心;如今,若在晋阳行大事,依李家的声威,只需您在这终南山里振臂一呼,遥遥相应,百姓必然景从!”
李三娘听闻,笑了笑,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儿,回道:”向先生,我乃女流之辈,岂能担此大任?”
向老翁摇摇头,说道:“若天降大任,岂分男女?何况,自北魏以来,李家的贤妻良母,知书达礼,智略过人,您的母亲,唐国公夫人,便是其中之一啊!若您能像老夫人在世时一样,果决能断,独撑大事,那么,岂止是这小小的南梦溪李家庄园可以保全?依民心,顺民意,能在八百里关中形成气候,与晋阳同进退共荣辱,也未可知啊!”
李三娘听闻,又悲又喜,悲的是母亲的音容笑貌又浮现眼前,喜的是走出困顿已初见曙光。
思索片刻,只见李三娘理了理襦裙,后退两步,弯腰一揖,说道:“向先生,‘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’,晚辈心中千般敬佩,万分感激!恳请先生辅佐晚辈,打开天地,经营终南,共赞父兄大业!”
向老者捋须点头,笑道:“老朽已年过七旬,黄土及项了,那堪抬举?待晋阳风云际会之时,只要您登高一呼,这终南山里的潜虎蛰豹,自然会弃暗投明,甘愿驱驰!”
夜风拂面,天色向晚,李三娘在门口拜别访客,望着老人拄仗远去的背景,心中已是有了格局……